在国际金融中心的版图中,离岸金融中心长期占据着独特且重要的位置。然而,部分观点对其存在诸多误解,将其描绘成充斥风险、脱离监管的“法外之地”,甚至视其为全球性赌场,这种片面认知严重阻碍了对离岸金融中心的客观理解与合理发展。事实上,离岸金融中心不仅是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助力我国构建完善国际金融体系的关键所在,理应得到重新审视与正名。
离岸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支撑
在全球金融格局中,顶尖国际金融中心均有相应的离岸金融中心为重要支撑:伦敦依托美元离岸交易市场成为全球最大外汇中心,日均美元交易量远超美国本土;纽约通过国际银行业设施(IBF)实现离在岸业务协同,强化全球定价权。
对我国而言,上海、深圳等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同样离不开与之匹配的离岸金融中心作为根基。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加速,离岸金融中心可为离岸人民币提供更广阔流通空间,提升其在国际支付、结算及投融资中的使用频率。通过开展离岸人民币债券、衍生品等业务,能吸引更多国际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增强货币影响力。同时,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便利,助力全球资源整合,提升我国在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
第一,国际金融中心与离岸金融中心的协同发展。国际金融中心与离岸金融中心的协同发展是全球金融格局的重要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资金流动与资源配置:离岸金融中心为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更广阔的资金来源和资源配置平台,促进了全球资金的高效流动。二是金融创新与业务拓展:离岸金融中心的有为监管环境为金融创新提供了空间,推动了国际金融中心的业务拓展和产品多样化。三是风险管理与市场稳定:离岸金融中心通过提供多元化的金融工具和服务,帮助国际金融中心的企业、投资者对冲风险和稳定了市场。
第二,离岸金融中心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提供人民币交易与投资平台:离岸金融中心为人民币提供了更广阔的交易与投资空间,吸引了更多国际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二是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通过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建设,提升人民币在国际支付、结算、投融资等领域的使用频率,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三是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离岸金融中心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便捷的金融服务,帮助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整合与投资布局。
离岸金融中心与离岸地:紧密交织的共生关系
离岸金融中心的运作与离岸地密不可分,这一强关联作用常被忽略。离岸地作为离岸金融中心的实体承载区域,以特殊制度环境支撑离岸金融活动: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通过极低税赋(甚至免税)、宽松监管政策,叠加政局稳定、基建完善等优势,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这种环境催生了离岸金融中心的繁荣:跨国公司纷纷在此设立子公司,借助优惠政策调配资金、开展投融资活动;企业通过注册特殊目的公司(SPV),高效完成跨境并购、资产证券化等操作,显著降低经营成本。
离岸金融中心与离岸地绝非孤立存在,而是二者相互赋能、共同发展的紧密联动的关系,共同构建起高效灵活的国际金融网络。
第一,离岸地的制度优势与吸引力。离岸地通过提供特殊的法律、税收和监管环境,成为离岸金融活动的重要平台,这些离岸地通常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低税率或免税政策。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等,对企业和个人的所得税、资本利得税等实行极低税率或完全免税,吸引了大量国际企业在此设立控股公司或金融工具公司,以优化全球税务结构。二是促进发展的金融监管。离岸地通常对金融机构的设立和运营要求与其本身的发展紧密联动起来,既关注风险防范,又重视本身的发展,始终在风险防范和促进发展之间寻求平衡,通过监管与发展的有机结合,达到简化审批流程、降低合规成本来促使金融机构能够更灵活地开展业务。三是完善的基础设施:离岸地一般具备先进的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以及专业的法律、会计和金融服务团队,为开展金融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第二,离岸金融中心的业务拓展与创新。离岸金融中心依托离岸地的制度优势,积极开展各类金融业务,包括但不限于:
一是跨境资金调配:跨国公司通过在离岸地设立资金池,集中管理全球资金,实现资金的高效调配和优化配置。二是国际投融资:离岸金融中心为国际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包括发行债券、股权融资等,同时为投资者提供多元化的投资渠道。三是风险管理与衍生品交易:金融机构在离岸金融中心开展外汇、利率、信用等衍生品交易,帮助企业和投资者对冲风险,稳定财务状况。四是资产证券化与结构化融资:通过将各类资产打包证券化,提高资产流动性,优化资产负债表,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
遵循国际规则的离岸金融中心运作
认为离岸金融中心不受监管、肆意妄为的观点与事实严重不符。当今各离岸金融中心均在全球金融监管趋严背景下,均在国际规则框架内运作、已形成多层次规范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监督指导其业务模式与风险管理,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将其纳入全球金融稳定监测范畴。在反洗钱与反恐融资领域,各离岸金融中心积极按照国际组织要求,与各国监管机构共享信息,建立严格的客户身份识别和交易监测机制。如开曼群岛金融管理局要求机构开展全面尽职调查,确保资金来源合法,可疑交易须及时上报。
税收监管方面,全球最低税率15%的全面实施与共同申报准则(CRS)的推行,不仅有效打击了恶意避税行为、更是对金融信息的监管进行了全覆盖。CRS更是极大推动了各国(地区)税务机关交换金融账户信息,不仅使离岸资金流动、资产及收益透明化,更是有效遏制了避税行为。可见,离岸金融中心是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重要参与者,绝非法外之地。
第一,国际监管框架的约束与规范。离岸金融中心的运作受到国际监管框架的严格约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反洗钱与反恐融资:离岸金融中心必须遵守国际反洗钱组织(如FATF)的标准,建立严格的客户身份识别和交易监测机制,防止资金的非法流动。因此离岸金融中心的每一分钱的流动,不仅都能溯源到资金的来源地、中间行和最终目的地,而且还能追踪到是哪个金融机构办理等明细信息。二是税收透明度:通过CRS等机制,离岸金融中心需与各国税务机关共享金融账户信息,确保纳税人的资产和收益信息透明化,防止恶意避税行为。三是金融稳定与风险监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等国际组织对离岸金融中心的业务模式、风险管理进行监督与指导,确保其不会对全球金融稳定构成威胁。
第二,离岸金融中心的合规与创新。离岸金融中心在遵循国际规则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合规与创新活动:
一是合规经营:离岸金融中心的金融机构严格遵守当地及国际相关法规,通过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确保业务稳健运行。二是金融创新:在合规的前提下,离岸金融中心不断推出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如各类离岸债券、绿色金融工具、数字金融产品等,满足市场多样化的需求。
“全球性赌场”之谬:被误解的成本洼地
将离岸金融中心比作“全球性赌场”,是对其功能与价值的严重歪曲。诚然,离岸金融中心凭借低税率、适度监管成为国际资金交易的成本洼地,但绝非不受约束的投机场所。
与赌场的纯粹投机本质不同,离岸金融中心的资金交易多基于真实经济需求:跨国企业在此调配资金,旨在优化全球产业链布局、开展跨境贸易投资;金融机构提供融资与风险管理服务,直接支撑实体经济发展。例如,新兴市场企业通过离岸中心上市、发债和融资,获得了安全的低成本资金,推动了当地基建与产业升级。在国际规则约束下,离岸金融中心对资金交易实施严格合规审查,从源头防范了非法流动与无序炒作。其交易规则虽灵活却有明确底线,绝非可随意操纵的“赌场”,而是为全球金融资源配置提供高效低成本平台,助力国际经济的繁荣和稳定。
第一,离岸金融中心的真实经济功能。离岸金融中心的资金交易并非纯粹的投机行为,而是基于真实的经济活动与商业需求,主要包括:
一是支持跨国企业全球布局:跨国公司通过在离岸金融中心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进行资金调配、投融资等活动,优化其全球产业链布局。二是促进新兴市场发展。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通过在离岸金融中心发行债券、获取贷款,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推动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三是提供金融服务与风险管理。金融机构在离岸金融中心提供融资、风险管理等服务,帮助企业、投资者对冲风险和稳定财务状况。
第二,离岸金融中心的合规审查与风险防控。离岸金融中心在国际规则的约束下,对资金交易有着严格的合规审查,从源头上防止了资金的非法流入与无序炒作:
一是客户身份识别与尽职调查:所有离岸金融中心的金融机构,都会按照监管规定对客户进行全面尽职调查(KYC),确保资金来源合法合规,而且能做到其每一分钱的资金流动都能完全掌握和了解,并对可疑交易及时上报和阻止。二是反洗钱与反恐融资机制:建立严格的反洗钱与反恐融资机制,与国际反洗钱组织紧密合作,提升对非法资金的甄别与拦截能力。三是税收透明度与信息共享:通过CRS等机制,与各国税务机关共享金融账户信息,确保纳税人的资产和收益信息透明化,防止恶意避税行为。
离岸金融中心并不天然伴随“巨大风险”
认为离岸金融中心天然伴随着五类巨大风险的观点,源于对其运行规则的缺乏了解。以我国金融机构的实践为例,建设银行在马来西亚纳闽的离岸金融中心开设了分行,中国银行在百慕大这个老牌的离岸金融中心设立了“分行”;这些布局并非盲目冒险,而是基于对当地金融环境、监管政策的深入研究与合理利用。这些金融机构在离岸金融中心开展业务时,均是严格遵守当地及国际相关法规、风险管理要求,确保业务的稳健运行。
第一,资本外逃风险的有效控制。所谓离岸金融中心可能成为资本外逃中转站的风险已成“过去时”。在当前全球金融监管加强的背景下,已得到有效控制。各国监管机构通过信息共享、联合监管等手段,能够实时监测资金流向,对异常资金流动及时预警与处置。
第二,金融风险的透明化与防范。利用离岸金融中心掩盖金融风险的说法也早已过时。现代企业财务信息披露制度不断完善,国际审计机构对企业财务状况严格审查,企图通过离岸金融中心隐匿债务、操纵财务报表的行为难以得逞。在逃避税费方面,全球最低税率与CRS的实施已让恶意避税无处遁形。至于洗钱风险,国际上离岸金融中心都在不断强化反洗钱措施,与国际反洗钱组织紧密合作,提升对非法资金的甄别与拦截能力。
我国离岸金融中心建设的战略布局
我国应充分认识到离岸金融中心的价值,积极推动离岸金融业务发展,在上海、深圳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符合国际标准的离岸金融中心,为我国建设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与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注入强大动力。具体措施包括:
制度创新与政策支持方面,一是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制度环境:以上海离岸经济功能区与深圳前海为核心,构建“准入便利、监管有效、税负合理”的制度环境,推动离岸金融业务的健康发展。二是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承诺制+全流程监管”改革,压缩审批时限,提升资金结算效率,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三是税收政策设计:实施“低税负+强监管”组合政策,吸引国际资本,同时防止恶意避税行为。
业务生态构建方面,一是聚焦实体经济需求:紧扣“一带一路”建设与企业“出海”需求,构建以人民币为核心的业务生态,确保离岸金融“从实体中来,到实体中去”。二是推动传统业务升级:重点发展离岸债券市场,提升跨境结算效率,推广“离岸结算+在岸风控”模式。三是创新业务突破:试点离岸人民币稳定币,开发离岸人民币利率互换、期权等衍生品,支持数字金融发展。
内外协同发展方面,一是构建“功能区+香港+全球节点”的联动网络:以上海离岸经济功能区为核心,联动香港离岸市场,拓展全球离岸金融服务中心,形成“功能区清算+区域服务”的全球网络。二是沪港、深港功能互补:实现三地离岸业务税收优惠互认,联合推出离岸债期货等对冲工具,降低跨市场交易成本。三是全球节点布局:在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区设立离岸金融服务中心,承接部分离岸业务需求,避免资金过度集中于上海,降低对在岸市场的直接冲击。
风险防控体系方面,一是构建“技术+制度”的立体防御体系:通过账户隔离、实时监测、跨境联合惩戒等措施,将风险锁定在可控范围。二是账户隔离机制:严格实施“内外分离型”账户管理,确保离岸业务不冲击在岸金融体系。三是科技赋能监测:积极运用“离岸金融风险热力图”,通过AI算法识别异常交易,提升风险预警精度。四是跨境联合惩戒:建立“离岸金融黑名单”制度,联合全球主要离岸中心实施跨境惩戒,提升违法成本。
生态支撑保障方面,一是建设我国自主可控的离岸地:在上海洋山港等地建设国际认可、符合我国监管要求和国际惯例的离岸地,明确在其注册的企业均有“非居民”属性;并在我国的离岸金融中心内制定鼓励这些“非居民”踊跃前来办理相关业务的特殊支持政策,并给予明确的税收优惠。二是国际化人才体系建设:吸引外籍金融人才,与国际金融中心签订职业资格互认协议,培养本土专业人才。三是高能级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上海自贸试验区升级为离岸经济功能区核心区,提升大宗商品定价能力,建设全球离岸金融数据港。四是长效政策保障:成立中央金融委主管的“离岸金融监管局”,统筹协调离岸事务,建立“离岸金融发展指数”,增强政策透明度与稳定性。
离岸金融中心的战略价值与未来展望
离岸金融中心绝非如部分观点所描述的那般充满风险与隐患,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离岸地紧密协作,在国际规则框架内有序运行,为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国际资本流动以及金融创新提供了关键平台。我国应充分认识到离岸金融中心的价值,积极推动离岸金融业务发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国际标准的离岸金融中心,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注入强大动力,在全球金融竞争中赢得主动。
当前,全球货币体系变革为离岸金融中心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一带一路”建设催生大量跨境金融需求,自贸试验区改革为制度创新提供载体。随着我国离岸金融中心制度体系的完善、业务生态的成熟、风险防控的强化,我国有望在未来十年建成与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既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核心支撑,也为全球离岸金融发展贡献“服务实体、风险可控、多元包容”的中国方案。
(作者景建国系上海金融业联合会专家、上海首席经济学家金融发展中心离岸金融研究所所长,唐铭煜系浦发银行嘉定支行风险经理。本文仅是个人意见,并不代表供职单位的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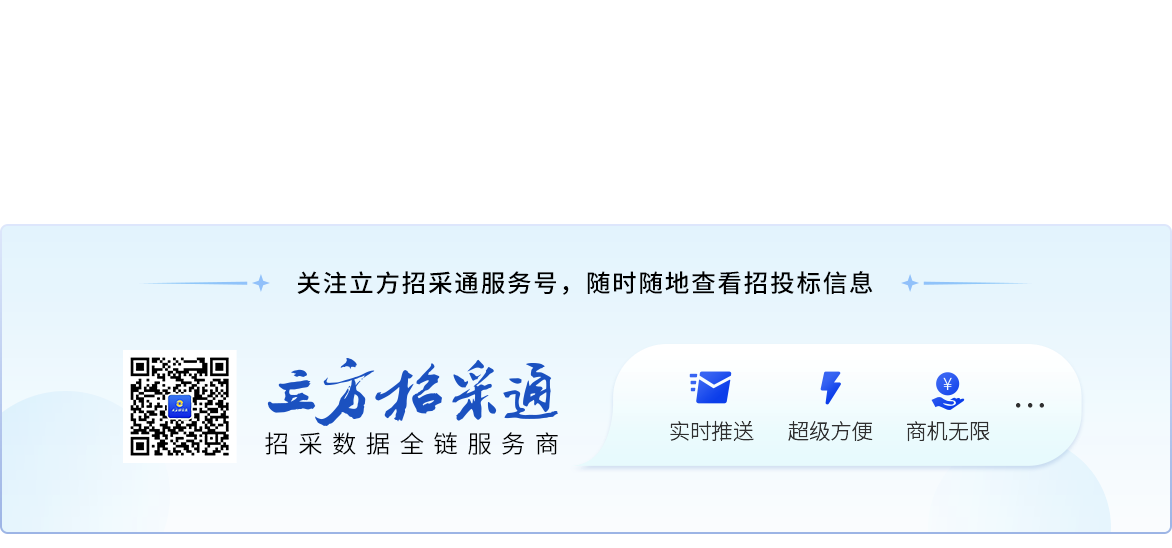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