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在“对等关税”相关安排中罗列出200多个谈判国家名单,其中18个国家与经济体是重点谈判对象。美国的亚洲盟友国几乎全部在列:除了与美国正式签署了双边同盟条约的日本、韩国、菲律宾与泰国,没有正式条约约束但实为紧密安全伙伴的新加坡、印度、越南与印度尼西亚也在名单中,而菲律宾、新加坡、越南与印度尼西亚还是东盟的核心成员国。因此,对于美国来说,即便面对的是所谓的盟友国,要想与其签署绝对有利于自己的单方面协议,概率并不大;同时,试图让所有谈判对手完全俯首臣服,也没有任何可能。
美国与日本:艰难的讨价还价
除了将日本汽车进口关税从2.5%大幅提高至25%之外,特朗普设定的90天谈判“缓冲期”内,还无一例外地对日本产品保留了10%的基本进口税率,而在“缓冲期”截止后,特朗普又宣布从8月1日起对日本进口产品征收25%的关税,当然,之前特朗普对全球钢铝征收50%的关税对日本同样有效,同时按照特朗普的说法,25%的关税不包括其他行业关税,也就是说,除对日本汽车和钢铝分别征收25%和50%的关税外,其他所有日本的总体关税率将达到35%(10%基本税率+25%新税率)。
日美已举行了七轮部长级贸易谈判,但至今依然没有打破僵局,原因是双方的诉求并没有得到满意的回应。就美方来说,除了坚持日本接受基础关税以及25%的汽车关税和50%的钢铝关税外,还提出了不少非关税要价,比如要求日本进一步开放农产品市场(日本牛肉关税47%)和限制汽车出口规模等,日方则要求美方一揽子取消所有新关税,尤其强调汽车关税与农产品市场开放是自己不可能破除的基本底线。
数据显示,去年日本对美汽车出口额约为400亿美元,占日本对美出口总额约28%,涉及约558万就业人口,同时汽车出口关联到电子、机械、化工等产业链,特别是广大的中小企业,它们是日本经济的毛细血管,若关税长期化,势必戕害日本经济的“心脏”;就农业而言,若日本开放农产品市场尤其是大米免税配额,等于就是自我摧毁了坚守半个世纪的农业保护体系,而更重要的是,以“农协”为代表的农业团体拥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是自民党数十年来的“铁票仓”,牺牲农业利益,等于自掘坟墓,任何内阁都将失去其生存基础。
自然,对于美国提出的所有条件,日本不会照单全收,但权衡之下,日本在谈判席上目前处于下风,只要美方能在汽车和农业领域蛮不讲理,日本可能会在其他方面多多少少地满足对方诉求,比如日本会增加在美国市场的投资尤其能源方面的投资,适当扩大美国大米、牛肉的进口配额,以及加强与美方在高端半导体生产、轮船和飞机制造等领域的合作等。在日本看来,自己在美已进行了大量投资,仅去年净投资额就达到11.7万亿日元,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同时,日本三大车企在美国本土生产汽车已超350万辆/年,综合创造了超300万的工作岗位,美国应该在关税上让日本享受到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待遇。
不过,对于日本的请求,特朗普不仅没有做出任何让步,反而警告称,如果日本对美国提出的“对等关税”作出反击,美国将在25%的基础上再提高同等额度的关税。数据显示,美国是日本第二大出口市场,对美顺差去年达到903亿美元,整体上对美国市场保持着非常强的依赖,更因为汽车出口的极端重要性,特朗普也算抓住了日本经济的“命门”;另一方面,虽然日本手中也掌握着号称“金融核弹”的1.13万亿美元美债,但也不敢大规模抛售,否则日元急速升值会反过来重创日本出口。也正是如此,日本一方面在口头强硬表示要捍卫自身利益,同时也主动寻求与美国的进一步谈判,哪怕是先获得美方的局部性、临时性豁免,日方也会感到满足,以此为基础,接下来双方可能会形成全面性的临时协议,且后续谈判完全破裂的可能性也不大。
美国与韩国:让步中求同
与日本一样,韩国也被列入新一轮加征“对等关税”的名单中,幅度同样是25%,而有所不同的是,特朗普对韩国的态度似乎要友好一点,因为初始美国是要对韩国进口商品开征26%“对等关税”的,但现在看来,谈判“暂缓期”满后特朗普开出的最新关税率降低了一个百分点。不过,特朗普也同时强调,如果韩国以提高“对等关税”作为回应,美国也将在25%的基础上再提高同等额度的关税,双方谈判呈现出的紧张形势似乎也没有实质性缓解。
目前来看,无论是已经开征高额关税的钢铁关税还是汽车关税,韩国对美方的作为均感到非常不爽,因此明确诉求是希望一切能够回到韩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范围之内,即双方都施行零关税,不过美方不仅对此无动于衷,相反将驻军费用问题也纳入谈判议题,而且要求韩国取消一些非关税障碍,比如取消技术标准、监管差异等隐性壁垒,同时指出韩国的农业检疫、汽车环保标准都存在“不公平竞争”,对此,韩国指出,贸易归贸易,防务归防务,二者不可捆绑挂钩,并提出“经济与安全分离”原则,不可借关税工具要求增加对2.85万驻韩美军的费用。
资料显示,韩国出口到美国的主要商品包括汽车、汽车零部件、半导体、药品、钢铁和机械,其中,去年韩国汽车对美出口额达到347亿美元,占整体汽车出口的49.1%,同时对美汽车零部件约135亿美元,占整个汽车零部件出口总额的36.5%,因此,仅汽车与汽车零部件对美出口规模就占了韩国对美出口总额的38%,而且美国还是韩国汽车的最大出口市场,自然也就称得上是韩国汽车业的生命给养地;另据韩国贸易协会数据,去年韩国半导体出口同比增长43.9%,达到1419亿美元,并创历史新高,其中对美半导体出口激增123%,达到107亿美元,虽然看上去占比不大,但若美国在加征关税的同时,就韩国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反复添堵,韩国半导体的日子自然也不好过。同样,2024年韩国对美钢铁出口额达87亿美元,占总出口的13.1%,若失去美国市场,也会感到割肉之痛。
总体看来,包括汽车、半导体与钢铁三大出口支柱,去年韩国收获了6838亿美元的货物贸易出口战绩,其中对美出口1278亿美元,占比约19%,并且韩国连续七年对美国出口创出新高,而更重要的是,2024年韩国对美贸易顺差达556亿美元,比2023年增长25%,同样创历史新高,这种情形之下,若特朗普硬是拿关税政策搞事,韩国经济无疑将遭遇巨大冲击。也正是如此,在与美国谈判过程中,韩国并没有表示出如同日本那样的强硬,反复释放的官方话语是,将尽最大努力与美国达成协议,谋求以韩国国家利益为中心、务实共赢的结果。
从谈判策略上看,韩国采取的是防御性妥协策略。一方面,韩国可能会接受10%基准关税,同时会在农产品市场开放上做出让步,如开放对美牛肉进口市场,并会增加对美国芯片设备和LNG能源的采购额,但另一方面也会拼命维护汽车与半导体出口底线,而作为回应,美国也有可能对韩国汽车出口关税做适当下调,同时豁免半导体部分关税。总体看来,韩美双方在谈判过程中都知道对方想要什么,因此,相比于同日本谈判,美国与韩国的谈判进程要顺利得多,彼此达成最终协议的时间也会早些。
美国与印度:各自获取最大化满足
起初美国对印度出口商品的关税要价是加征26%,当然这并不包括10%的基本关税以及汽车和钢铁等行业关税,因此,就影响面较大的“对等关税”而言,美国对印度产品的总体关税率至少会提高到36%。尽管在特朗普抛出的最新一轮“对等关税”名单中,印度并不在其列,美国也没有像对待欧盟、加拿大那样,单独对印度点名加征新的“对等关税”,但这并不等于对印度网开一面,维持原来的决定,对于印度来说同样是难以承受之重。
在开出总体关税率的同时,美国对印度的要求非常清晰。一方面,美国要求印度降低纺织品、珠宝、海鲜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关税,同时削减汽车、葡萄酒和化工品进口壁垒;另一方面,美国提出希望印度扩大苹果、坚果、以及转基因玉米、大豆等农产品市场准入,并接受“永久性农产品关税削减”而非临时配额;就印度诉求来看,除了要求美方有针对性削减钢铁50%高关税之外,更希望美国能够对印度商品的关税税率低于面向越南等国的关税税率,同时确保纺织品、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持续市场准入,不仅如此,印度也坚决拒绝全面开放农产品市场。
因此,美印双方谈判的最大堵点来自于印度的农业保护方面。在印度政府看来,农业和乳制品是不可践踏的红线,这不仅仅是关乎到本国“粮食安全和影响农村生计”问题,更是莫迪政府能否持续的执政的关键所在。资料显示,在印度与美国展开谈判过程中,印度农民联盟已发起多次全国抗议有活动,反对农业开放;印度农民数量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之多,莫迪要想赢得2029年大选农票仓,不能不在农产品市场开放上持非常谨慎的态度,由此也决定了印度政府在该领域能够做出的妥协空间极为有限。
但是,莫迪政府也必须要考虑印度对美国出口严重依赖的客观事实。数据显示,2024年印度商品出口额3741亿美元,其中对美商品出口为865亿美元,作为印度出口的第一大市场,美国的贡献占比达23%,砍掉这一块,印度经济肯定有“失血”般剧痛;另外,印度还可从美国市场取得412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出口创汇能力也严重依赖美国市场。基于此,自关税摩擦以来,印度一直在美国面前保持着弱者求存的姿态,即便是宣布要对部分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官方通告中也会在前面特地加上已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的明确语句,以避免进一步惹怒美国。
鉴于以上情况,印美谈判中印度自然处于较为被动的位置,寻求达成贸易协定的态度也会主动些。经过前一阶段的磋商,目前美国与印度已就数千项商品关税削减达成初步共识,其中印度在工业品关税如汽车、化学品等方面做出了让步,同时承诺扩大美国能源进口,而在农产品市场开放方面,接下里印度让步的最大的可能性是开放“非敏感品类”(如杏仁)进口市场,至于小麦、乳品市场开放,美国也可能不会过度施压,在印度对目前13%的平均关税做出相应降低的同时,美国也会适当调低印度的钢铁出口关税,并在纺织品配额上给予印度更多的优惠。
美国与东盟:缺口已经撕开
东盟10国作为一个贸易整体,成员结构较为复杂,美国也非常清楚与同盟展开集约性谈判的可能性不大,且实际效果也非常之小,于是选择了各个击破的方针;不仅如此,对于东盟各成员国,美国宣布的最新一轮“对等关税”,也采取了差异化策略,其中涉及的部分国家中,马来西亚、柬埔寨和泰国以及老挝与缅甸,分别被课以25%、36%和40%的关税,该策略的阴谋在于,首先倒逼像老挝与缅甸这样的经济落后国家率先主动要求与美国谈判,由此引导其他国家发出同样的诉求。
截至目前,越南与印度尼西亚已与美国达成了谈判贸易协定,前者接受了美国20%进口关税的要求,同时对美国出口商品实施零关税,后者也愿意向美国缴纳19%的出口商品关税,并承诺不对美国出口商品征税,二者让步尺度之大一目了然。分析发现,2024年越南GDP仅为4763亿美元,但进出口金额高达7862亿美元,其中出口4055亿美元,进口3807亿美元,是典型两头在外的国家,而且出口依赖比重高达85%;更为严重的是,越南对美国的出口额达1196亿美元,占越南总出口额的29.5%,对美国贸易顺差为933亿美元,严重依赖美国,而与越南并行,印尼也有着同样的对外依赖症,双方急于与美国达成退让性协议自然也就不难理解。
就美方对东盟的整体诉求而言,在要求东盟成员国接受不同程度“对等关税”的同时,也希望东盟全面取消农产品以及数字贸易壁垒,并减少对华中间品依赖。数据显示,去年东盟对美国出口总额达3586亿美元,约占其总出口额的15%,若美国开征“对等关税”,对区域经济冲击显然不小,尤其是东盟的汽车、电子、纺织三大核心产业,年损失或超1600亿美元。另一方面,在对待特朗普关税政策上,虽然东盟一直在强调要保持区内团结统一,但其实内部的态度分化格外明显,其中越南和柬埔寨属于妥协派,表示愿意以“单边零关税”换取20%左右的出口税率,而马来西亚、老挝属于抵抗派,拒绝开放有关经济作物的市场,并同时积极寻求与中国的合作,而泰国与新加坡等属于观望派,最终,东盟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各成员国与美国进行灵活性谈判。
总体而言,美方与东盟会形成分层协议,后者中的成员国对美国作出的让步也各不相同,其中柬埔寨最有可能复制越南和印尼模式,新加坡和泰国会答应增加对美国的能源、飞机采购量,以换取美国适度削减“对等关税”,而对于马来西亚和老挝来说,不得已的情况下可能开放部分农产品与经济作物产品市场,如泰国的小米市场,印尼的棕榈油市场,同时换取美方对纺织品等产品的关税豁免。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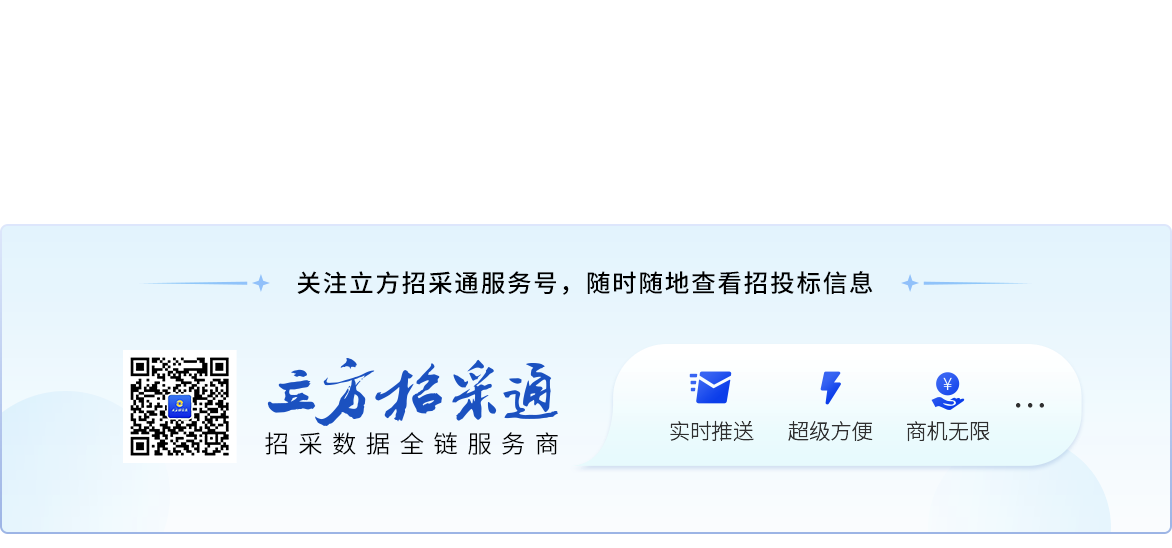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