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为我国离岸金融发展指明了战略方向。
离岸金融体系是国家金融竞争力的核心载体,核心价值在于全球资金流动中的“定价规则、配置资源、制度输出”,而非单纯吸引资金。它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升全球金融治理能力的必由之路,更是我国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跨越的关键支撑。体系构建需以鲜活业务实践为根基,借鉴伦敦、新加坡等国际离岸中心经验,坚持“实践为基、政策为翼”,打造适配我国国情的离岸金融生态。
制度生态系统的系统性重构
离岸金融体系并非“境外账户+外币业务”的简单组合,而是融合五大维度的制度生态系统:
金融维度,涵盖OSA(
制度维度,包含法律适用、司法仲裁、监管规则、税收政策、合规标准。
治理维度,涉及跨境监管协同、数据治理、反洗钱、反避税、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
空间维度,依托离岸金融功能区、国际金融中心、跨境合作平台。
战略维度,服务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建设,对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规则,需通过自贸试验区试点验证规则可行性。
从“资金洼地”到“制度高地”,离岸金融体系的核心作用体现在三方面:
制度定价权,推动人民币计价资产成为全球配置工具,确立人民币国际定价权。
资源配置力,优化全球资本效率,支撑“一带一路”与区域经济合作,服务实体经济。
规则输出力,将我国数字货币监管、绿色金融等制度经验转化为国际规则,提升全球金融治理话语权,且规则需源于业务实践,如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需先试点验证企业体验。
制度供给滞后于战略需求
制度碎片化,缺乏系统设计。离岸金融试点多为“单点突破”(如离岸债、FT账户),无统一法律框架,导致“政策补丁化、监管碎片化”。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为例,各区域政策协同不足,未形成“中央统筹+地方立法+区域协同”机制,且缺乏“实践—反馈—优化”循环,政策调整滞后于市场需求。
法律国际化程度低,认可度不足。国际商事合同适用中国内地法律比例仅12%,仲裁裁决执行率72%,远低于中国香港的89%和95%,制约非居民参与意愿。现有法律未充分吸纳离岸业务纠纷案例(如跨境信托确权争议),法律适用缺乏实践支撑。
账户体系功能受限,离在岸隔离过度。FT账户因兼顾离在岸功能,存在“风险隔离不足+效率低下”问题;OSA账户虽纯离岸,却无法开展人民币业务,制约人民币国际化。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账户仍局限于外币业务,未借鉴2013—2018年“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突破6000亿美元的经验,离岸人民币业务滞后严重。
税制缺乏竞争力,吸引力不足。中国内地离岸主体税负高于中国香港、新加坡,缺乏差异化优惠,导致“资金转道出境”。上海自贸试验区税收优惠无系统性设计,未像海南自贸港试点“离岸绿色债券利息免税”那样,收集国际机构参与数据,税制调整脱离市场实际需求。
法律供给滞后,立法空白。1997年《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未涵盖保险、证券等业务,法律效力层级低。我国离岸金融立法无系统框架,且脱离业务实践,导致离岸银行业务规模从峰值620亿美元降至500亿美元。
制度生态系统全面优化提升
战略定位:从“资金洼地”到“制度高地”。摒弃“避税港”模式,构建“制度型离岸金融中心”,以人民币国际化为主线,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制度型开放试验田”。这需依托具体的业务实践来验证定位的可行性,如上海临港新片区2023年32家银行办理离岸业务4.2万亿美元,为人民币资产配置提供实践数据。
制度架构:“1+N+X”体系。“1”是指制定《离岸金融法》:作为基本法明确法律地位、监管框架等,制定前需在自贸试验区开展3—5年试点,积累多元业务数据,借鉴伦敦30年、新加坡10年实践经验,避免重蹈东京“无实践就立法”导致市场萎缩的覆辙。
“N”是指专项业务制度:围绕离岸债券、离岸保险等制定管理办法;如《离岸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可参考深圳前海“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8600亿元实践,明确额度与信息披露等规则。
“X”是指地方差异化试点:授权上海浦东、海南自贸港等开展地方立法,如上海探索离岸税收优惠、海南试点营商环境优化,形成“区域试点—全国推广”路径。
法律适用:设立“离岸法律适用区”。在上海临港新片区等区域允许国际商事合同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规则,目标普通法适用率70%、仲裁裁决执行率95%,国际仲裁员占比超50%。需基于离岸商事纠纷案例(如离岸租赁争议)完善规则,避免脱离实际。
账户体系:升级“本外币合一”新型OSA体系。以OSA账户为基础,纳入人民币业务,实现“自由兑换+风险隔离”,对接SWIFT(国际资金清算系统)、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数字人民币系统。先在上海自贸试验区试点,借鉴“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实践,验证规则可行性。
税制优化:“全球最低税率+离岸差异化”。对接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全球最低税(15%),对离岸债券利息、基金收益等免征或递延纳税。海南自贸港可先试点“离岸绿色债券利息免税”,收集国际机构数据,避免政策脱离市场。
“六位一体”生态集成创新
需跳出“就金融谈金融”,构建“金融+法律+税收+治理+空间+国际规则”生态:

金融维度:多层次产品矩阵。布局基础产品(离岸债券、航运保险)、创新工具(离岸数字资产、绿色衍生品)、特色服务(离岸租赁、离岸信托),如临港新片区“离岸债券+租赁”产品、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1.2个百分点。
法律维度:适配法治框架。试点《离岸金融法》,设立离岸仲裁中心,允许适用国际法律,基于实践案例完善规则,避免东京式限制的问题。
税收维度:优惠与合规平衡。实施“离岸企业所得税15%”“利息收入免税”,落实CRS(共同申报准则)信息交换,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
治理维度:包容审慎监管。推广监管沙盒,建立跨境监管协作,实时监控离岸资金流动,如深圳前海平台将异常交易占比控制在0.3%以下。
空间维度:错位承载。以上海临港为核心,海南、前海等错位发展,依托港口联动“港口经济—离岸金融”,如临港2023年离岸船舶租赁占全国35%。
国际规则维度:深度对接。对接CPTPP跨境服务负面清单,采用IFRS准则,参与OECD规则制定,“中国方案”需源于实践,如数字人民币试点经验。
建设中国特色离岸金融体系
制度自信:拒绝移植,坚持再造。不复制港澳模式,以人民币国际化为主线,构建“规则输出型”体系,如数字人民币创新需先试点收集企业数据,形成特色制度。
制度输出:从“接受者”到“制定者”。推动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输出数字货币监管等经验,如上海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试点需形成系统机制,规则输出需基于实践案例。
以制度型开放引领未来
离岸金融体系建设是制度重构与战略跃迁的系统工程,需以党中央指示为遵循,以上海、海南等为试验田,坚持“实践为基、政策为翼”。通过“实践—反馈—优化”循环,积累5万亿美元以上实践数据,推动生态从“框架构建”到“功能成熟”,形成兼具中国特色与国际竞争力的新模式,支撑我国向金融强国跨越。
(作者系上海金融业联合会专家、上海首席经济学家金融发展中心离岸金融研究所所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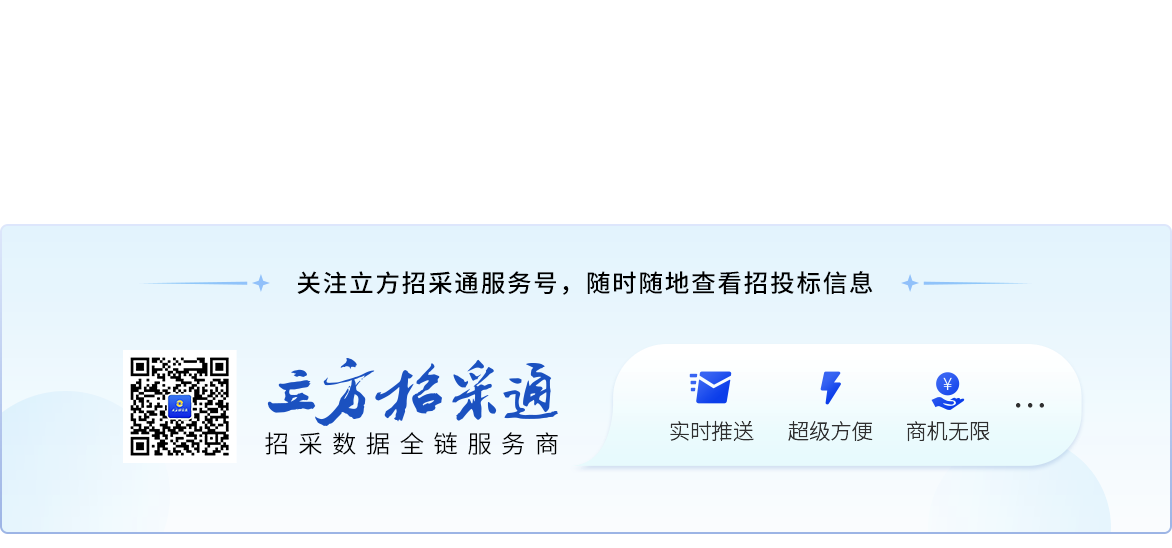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





